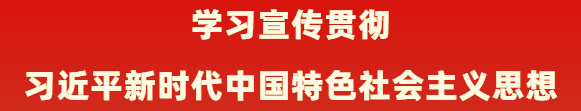- 當(dāng)前位置:豐澤新聞網(wǎng) > 文化旅游 >
清晨,日光灑向蚵殼厝,伴隨“咯吱”聲,一道木棧門被打開。 店家一邊搬出簪花,一邊將掛滿蟳埔特色服飾的長(zhǎng)衣架推到院子中央。此刻,遠(yuǎn)道而來的游客早已等候多時(shí)。盡管是工作日,小巷仍被擠得水泄不通,房前屋后回蕩著拍照的快門聲。 蟳埔村地處福建泉州灣入海口,自古以打魚販魚為業(yè),知名度不高,自然風(fēng)光在擁有眾多海灘港口的福建也并不“出挑”。然而自今年春節(jié)起,原本安靜的小漁村卻因?yàn)椤耙欢浠ā睙狒[起來。 慕名而來的游客戴上簪花,穿上特色服飾,站立在蚵殼厝旁,只為體驗(yàn)當(dāng)一天“蟳埔姑娘”。據(jù)統(tǒng)計(jì),蟳埔村節(jié)假日日均游客量一度達(dá)到5萬人次。 一個(gè)草根漁村何以“一夜走紅”?答案或許不在山水風(fēng)光,而在代代相傳的民俗文化之中。
體驗(yàn)“簪花圍”的游客在泉州市蟳埔村拍照。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周義 攝 草根漁村“一夜花開”的奇跡 已是冬日,蟳埔村里依舊“百花盛開”。街道巷陌,處處是頭戴簪花的游客,放眼望去,人頭攢動(dòng)如同一座“流動(dòng)的花園”。 就在一年前,這里還是一個(gè)少人關(guān)注的村落。走進(jìn)村里,空氣彌漫著海的氣味,上了年紀(jì)的婦人會(huì)在發(fā)髻中插上三兩朵紅花,來街邊售賣漁獲。由于鮮少外人來訪,村民們習(xí)慣用閩南語交流。 蟳埔村的“爆紅”來自今年春節(jié)前的一次“偶然”。彼時(shí),演員趙麗穎為國(guó)內(nèi)某雜志拍攝了一組以蟳埔女頭飾為靈感的時(shí)尚大片,古樸新穎的造型在網(wǎng)絡(luò)上引發(fā)熱議,也將“蟳埔”這個(gè)生僻的名字帶入公眾視野。許多游客紛紛打開地圖,尋找這個(gè)村莊。 “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都來蟳埔了。”村民莊群打趣道,原先村里只有零星幾家簪花鋪,蟳埔女走紅后,來插花的人絡(luò)繹不絕,店鋪增加到100多家。作為村里最早一批開設(shè)簪花鋪的村民,今年旺季時(shí),莊群每天接待上百號(hào)顧客,為了應(yīng)付繁忙局面,83歲的母親也得一同上陣。 插花過程看起來繁復(fù),可對(duì)老一輩蟳埔人來說卻是尋常。作為與惠安女、湄洲女并稱的“福建三大漁女”,每逢喜慶節(jié)日,蟳埔女都會(huì)將頭發(fā)盤成海螺狀,橫穿一支象牙簪,再在四周細(xì)細(xì)插上一圈不同顏色的簪花。因形似孔雀開屏,這一古老民俗又被稱為“簪花圍”。 “在蟳埔女的成長(zhǎng)軌跡里,花是代表祝福的信物。”莊群告訴記者,從小孩滿月到行成人禮,再到談婚論嫁,每逢人生重要節(jié)點(diǎn),蟳埔女都要互相贈(zèng)花,五顏六色的花戴在頭上,喜事的氛圍也濃了幾分。 至于簪發(fā)戴花的由來,有人說是蟳埔女保留古代“骨針安發(fā)”的風(fēng)俗,也有人說“簪花圍”源于中亞婦女戴花的習(xí)俗,在宋元時(shí)期由海上絲綢之路交流帶來。 漁村“出圈”的招牌除了簪花,還有紅白相間的蚵殼厝。在插好花之后,一些游客會(huì)順勢(shì)倚身在蚵殼厝邊合影留念,魚鱗般的蚵殼墻映襯著五彩花朵,別有民俗之美。 對(duì)蚵殼厝頗有研究的蟳埔社區(qū)老人協(xié)會(huì)原會(huì)長(zhǎng)黃榮輝說,蚵殼就是牡蠣殼,蚵殼厝墻體是由白色的牡蠣殼和紅磚共同砌成。這些牡蠣殼并非泉州原產(chǎn),而是“海絲”遺珍。宋元時(shí)期,滿載著絲綢、茶葉、瓷器的遠(yuǎn)洋商船從泉州駛向世界各地,從非洲東海岸空船返航時(shí),為避免重心不穩(wěn),船員將異域海灘上的大蚵殼搬上船作為壓艙物運(yùn)回泉州。 當(dāng)?shù)卮迕裼眠@些越洋而來的蚵殼建造起“不怕滲水、不怕海風(fēng)侵蝕、冬暖夏涼”的蚵殼厝。過去,它們向海而立,送別過往水手、商人和探險(xiǎn)家,在潮漲潮落間守候商船往來、貿(mào)易通達(dá);今天,它們屹立海風(fēng)中,向后人講述那段厚重的海絲傳奇。 蟳埔社區(qū)黨支部書記黃向東介紹,今年春節(jié)以前,蟳埔村并非傳統(tǒng)熱門旅游地,但春節(jié)后,面積僅3.8平方公里的村子日均客流量達(dá)幾千人次,且熱度越來越高,“五一”期間每天有2萬多游客,到了國(guó)慶更是攀升至5萬人次,比肩同期的廈門鼓浪嶼。 大量涌入的游客改變了村莊數(shù)百年來的生產(chǎn)生活方式。一些留守在村里挖海蠣的老人,帶著老手藝上崗成了簪花師傅,旺季時(shí)一天能有數(shù)百元的工資收入;在外工作的年輕人回到村里,將漢服、馬面裙等傳統(tǒng)服飾引入造型搭配,當(dāng)起了“造型師”;1.6公里的海岸線上,海鮮酒樓生意火爆,也帶動(dòng)了村中舊厝的租金收入…… “今年旅游業(yè)的爆火,每家每戶平均增收約有30%以上。”黃向東說。長(zhǎng)久以來,身處泉州市中心的環(huán)灣經(jīng)濟(jì)帶,蟳埔村更像個(gè)“世外桃源”——村外高樓林立,村里依然保留著古樸的石頭厝,村民們也常年保持著男人出海捕撈、女人灘涂養(yǎng)殖的傳統(tǒng)勞作方式,收入來源單一。眼下,隨著旅游業(yè)崛起,這一切正悄然而變。
蟳埔少女12歲起即可盤發(fā)戴花 (張旭 攝) 一場(chǎng)未雨綢繆的“護(hù)花保衛(wèi)戰(zhàn)” 今年是蟳埔文旅誕生奇跡的一年,但這種走紅并非無跡可尋。早在十多年前,當(dāng)?shù)卣团c居民共同打響了一場(chǎng)民俗保衛(wèi)行動(dòng),為今天“蟳埔花開”播下種子。 蟳埔女金飾制作技藝非遺傳承人王勇躍記得,過去,花在蟳埔人的生活中有著別樣的意義,“我們講究‘以花為禮’,出門做客時(shí)插上花,是對(duì)主人家的尊重;請(qǐng)客的時(shí)候,主人家會(huì)根據(jù)親疏遠(yuǎn)近分配花朵,誰頭上的花最多,代表誰是最親近的。” 這樣的故事過去在蟳埔時(shí)常發(fā)生,花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。 然而,進(jìn)入上世紀(jì)90年代,外來文化沖擊了漁村的傳統(tǒng)審美。“一段時(shí)間里,街上看不到年輕人戴花,一來盤頭比較麻煩,二來大家覺得裝扮過時(shí)老氣,跟不上潮流。”王勇躍說,隨著年輕人褪去簪花和金飾,染上新潮的發(fā)色,“花”成了老一輩人的專屬記憶。 察覺到這一微妙變化,當(dāng)?shù)卣芸齑蝽懥艘粓?chǎng)民俗保衛(wèi)戰(zhàn)。2008年以“簪花圍”為代表的蟳埔女習(xí)俗被列入第二批國(guó)家級(jí)非遺名錄,在泉州各級(jí)政府宣傳推動(dòng)下,每年有三十多批次來自國(guó)內(nèi)外的新聞媒體、采風(fēng)團(tuán)、專家學(xué)者等來蟳埔拍攝、調(diào)研。 2013年,泉州市出臺(tái)《蟳埔民俗文化村保護(hù)整治規(guī)劃》,對(duì)蟳埔女發(fā)飾服飾、蚵殼厝等民俗資源出臺(tái)保護(hù)措施,安排專項(xiàng)資金保護(hù)修葺傳統(tǒng)建筑,嚴(yán)格控制與傳統(tǒng)文化保護(hù)無關(guān)的新建或改建項(xiàng)目。 2019年6月,蟳埔舉行“最美簪花圍、海絲后花園”首屆蟳埔女盤頭大賽,由此誕生了一群“簪花圍”技藝大師。 今年62歲的黃晨是“簪花圍”國(guó)家級(jí)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唯一的省級(jí)代表性傳承人。在他的裁縫鋪里,有各個(gè)年代款式不同的蟳埔女服飾,它們都由黃晨一針一線親手縫制,青、藍(lán)為主調(diào)的版式既有年代感,又頗具時(shí)尚氣息。 裁縫鋪見證了蟳埔民俗變遷。黃晨說,20多年前,村里年輕人紛紛穿起了“喇叭褲”,傳統(tǒng)服飾幾無市場(chǎng),一籌莫展之際,當(dāng)?shù)卣贿呇a(bǔ)貼店鋪經(jīng)營(yíng),一邊組織腰鼓隊(duì)身著傳統(tǒng)服飾外出表演,幫助這一非遺文化存活發(fā)展。 為了發(fā)揚(yáng)民俗文化,他還走出村莊,在泉州黎明職業(yè)大學(xué)服裝專業(yè)、泉州濱海小學(xué)以特聘教師的身份授課。“更希望來蟳埔的游客不僅僅是為了拍照,而是真正喜歡我們的民俗內(nèi)涵。”黃晨說。 參與這場(chǎng)民俗保衛(wèi)行動(dòng)的不止有政府,還有許多民間志愿者。 34歲的黃麗泳是新一代蟳埔女,如今她更為人熟知的身份,是“為演員趙麗穎簪花的黃老師”。 “奶奶從小教導(dǎo)我們,蟳埔女頭發(fā)很珍貴,一定要梳頭盤頭。”黃麗泳從小耳濡目染學(xué)習(xí)簪花,在她看來,這一代人有責(zé)任拯救這項(xiàng)文化遺產(chǎn)。 十多年來,她把傳承和推廣蟳埔文化作為自己的使命。過去,她是幼兒園教師,平日里給孩子們梳頭簪花時(shí),會(huì)拍下美美的照片發(fā)到網(wǎng)上;后來,她辭去工作,跟隨文旅部門到各地參加推介會(huì)、文博會(huì),戴上頭飾向外推介“簪花圍”。年輕一代蟳埔人的長(zhǎng)期堅(jiān)守和推介,締造了今天“簪花圍”在社交平臺(tái)的“出圈奇跡”。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蟳埔人終于等來了“春暖花開”。黃麗泳觀察到,以往,蟳埔阿姨在鏡頭前都羞于表現(xiàn)甚至極力回避;而如今,老一輩人紛紛拾起傳統(tǒng)手藝,開小船的爺爺、挖海蠣的奶奶告別了風(fēng)吹日曬,在家里上崗就業(yè),面對(duì)鏡頭,大家的眼里多了幾分從容與欣喜。
圖片來泉游客紛紛打卡蟳埔(張旭 攝) 從“爆紅”到“長(zhǎng)紅”,蟳埔如何“花開不敗” 蟳埔村“出圈”,既有明星效應(yīng)的偶然因素,也有人文經(jīng)濟(jì)的必然邏輯。 近年來,放眼全國(guó),類似蟳埔的文旅奇跡并不罕見。從山西平遙古城的清漢晉商少奶奶,到貴州千戶苗寨的苗族少女,再到甘肅敦煌的西域公主,民俗服飾的旅拍經(jīng)濟(jì)熱,折射出這一代青年的文化追尋。 然而熱風(fēng)到底能刮多久?是轉(zhuǎn)瞬即逝的“網(wǎng)紅經(jīng)濟(jì)”,還是持續(xù)火熱的“文化密碼”?未來,還有諸多課題擺在蟳埔面前。 “我們格外珍視這來之不易的人氣。”泉州市豐澤區(qū)東海街道黨工委副書記陳培養(yǎng)告訴記者,為避免“亂砍價(jià)”“宰客”現(xiàn)象發(fā)生,政府層面多次召開會(huì)議規(guī)范簪花、餐飲等業(yè)態(tài)的價(jià)格。2016年“簪花+服飾”的體驗(yàn)費(fèi)用為40元,該價(jià)格標(biāo)準(zhǔn)一直延續(xù)到現(xiàn)在。節(jié)假日前夕,街道社區(qū)和豐澤區(qū)市場(chǎng)監(jiān)管局都會(huì)對(duì)海鮮酒樓開展不定期抽查,避免出現(xiàn)漫天要價(jià)的情況。 一地走紅,最受考驗(yàn)的是地方政府立足長(zhǎng)遠(yuǎn)的服務(wù)和管理能力。今年“五一”“十一”等前夕,東海街道為應(yīng)對(duì)客流高峰還提出了“一攬子”方案,包括成立臨時(shí)指揮部、優(yōu)化停車環(huán)境、加強(qiáng)占道經(jīng)營(yíng)整治、提供微公交接駁服務(wù),以及制作旅游導(dǎo)覽圖和停車場(chǎng)、公廁等基礎(chǔ)設(shè)施導(dǎo)向牌等等,幫助蟳埔平穩(wěn)應(yīng)對(duì)客流高峰。 采訪中,當(dāng)?shù)毓芾碚咂毡楸磉_(dá)了一個(gè)共識(shí):“爆紅”不是終點(diǎn),蟳埔的挑戰(zhàn)才剛剛開始。不同于其他鄉(xiāng)村“自上而下”的規(guī)劃,以蟳埔為代表的民俗村走紅,更多源于“野生自發(fā)”的力量,對(duì)地方治理而言,從“爆紅”走向“長(zhǎng)紅”,既要做好業(yè)態(tài)挖掘、商業(yè)推廣、文創(chuàng)開發(fā)等“謀篇長(zhǎng)遠(yuǎn)”的布局,也要做好村貌規(guī)劃、人員培訓(xùn)、基礎(chǔ)設(shè)施改造等“查缺補(bǔ)遺”的工作。 記者在村里走訪發(fā)現(xiàn),目前蟳埔的文旅業(yè)態(tài)還較為單一,部分簪花店雖然銷售一些文創(chuàng)產(chǎn)品,但種類和品質(zhì)都還有待提高。“蟳埔因文而興,未來應(yīng)進(jìn)一步做好文化這篇文章。”福建社科院副院長(zhǎng)黃茂興建議,蟳埔村屬于閩南文化生態(tài)整體性保護(hù)示范點(diǎn),媽祖文化、“海絲”文化內(nèi)涵豐富,未來可通過校企合作、金融支持等,扶持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創(chuàng)企業(yè),提供更加多元的文創(chuàng)產(chǎn)品豐富旅游業(yè)態(tài)。 福建師范大學(xué)旅游學(xué)院副院長(zhǎng)林明水認(rèn)為,蟳埔還需改變傳統(tǒng)文化生態(tài)“農(nóng)耕時(shí)代”面貌,做好文旅融合和基礎(chǔ)設(shè)施規(guī)劃。蟳埔村過去是個(gè)漁村,在轉(zhuǎn)型旅游的道路上,“欠賬”問題難以回避,新舊生產(chǎn)方式轉(zhuǎn)型過程的“較量”也有待化解。 例如,村中電線桿林立、一些村民占道經(jīng)營(yíng)等,經(jīng)當(dāng)?shù)馗刹恳龑?dǎo)方有轉(zhuǎn)變。未來,一方面需統(tǒng)一制定方案,對(duì)蟳埔民俗文化村核心保護(hù)區(qū)內(nèi)的街巷、房屋進(jìn)行保護(hù)性修復(fù),避免群眾無序開發(fā);另一方面,可對(duì)現(xiàn)有道路、碼頭等進(jìn)行適當(dāng)提升,協(xié)調(diào)電力部門做好電纜入地工作,并引導(dǎo)漁民到農(nóng)貿(mào)市場(chǎng)按規(guī)劃經(jīng)營(yíng),優(yōu)化游客入村整體體驗(yàn)。 “不被客流沖昏頭腦,小心呵護(hù)原生態(tài)的民俗風(fēng)貌,又不斷挖掘新的業(yè)態(tài),相信蟳埔會(huì)長(zhǎng)紅下去。”陳培養(yǎng)說。 傍晚,早冬的海風(fēng)呼呼吹過,海平面的紅潮被深藍(lán)蓋去,蚵殼厝前亮起橘色的燈光。頭戴簪花的老人送別最后一撥客人,仍意猶未盡地捻著手中的簪花。這些承載著祝福的花兒穿越時(shí)空,在蟳埔人的發(fā)髻端頭,迎接新的春天。 記者:吳劍鋒 周義 龐夢(mèng)霞 |
- 關(guān)于我們/廣告服務(wù)/法律顧問
- 閩ICP備案號(hào)(閩ICP備05022042號(hào))
- 泉州市豐澤區(qū)融媒體中心 地址:泉州市津準(zhǔn)街31號(hào)
- 郵政編碼:362000 聯(lián)系電話:0595-22505096
- 不良信息舉報(bào)電話:0595-22505995 舉報(bào)郵箱:fzqwxb@163.com
- 福建省新聞道德委舉報(bào)電話:0591-87275327
- 泉州市豐澤區(qū)版權(quán)所有 未經(jīng)授權(quán),不得轉(zhuǎn)載或建立鏡像